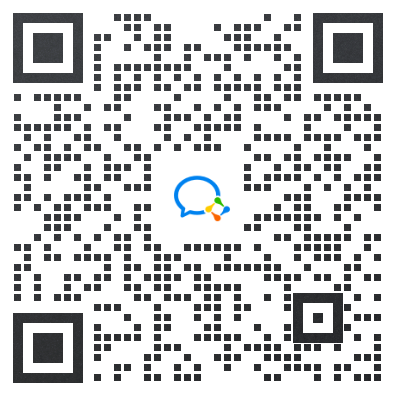【2021遴选政策理论】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初心(2)
西方标榜的“选举民主”实际是一种“残缺的民主”
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西方国家无力进行社会革命,又要借助民主话语增加统治合法性,只能对原本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进行狭义化理解:先是将经济与政治内涵彼此剥离,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是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斯图亚特·密尔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则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并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在此,“人民的统治”已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西方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部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以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脱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使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从实践看,西方民主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有一定进步意义,如公众参政范围扩大,公民主体性增强等。但随着时代发展,西式民主的缺陷日趋暴露出来。尤其在贫富悬殊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
理论上说,在实行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可以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
讽刺的是,西式民主明明在西方国家治理实践中百弊丛生,暴露出诸多问题,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仍然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已经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美国的西方盟友也对美式民主丧失信心。2021年5月,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和民主国家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对5万多人进行的“2021年民主认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担心美国对本国民主构成威胁,5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美国是非民主国家,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代表少数集团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