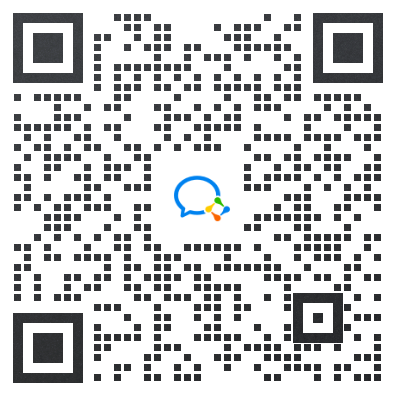【2021遴选政策理论】民粹主义的“概念过载”与西方制度困境(1)
历经波折和反转的美国大选代表了民粹主义浪潮的一次转折,但特朗普所获得的选票数仍反映出民粹主义势力不可低估。正如《外交事务》杂志中《默克尔对中国及世界的看法》一文所指出的,“真正让柏林感到震撼的是特朗普所拿到的7420万张选票,特朗普的追随者并不会随着特朗普下台而消失,其他人接过特朗普的政治模式只是时间问题”。基于对民粹主义政治卷土重来的担忧,西方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的集中揭露和批判正在掀起新一轮高潮。但值得关注的是,民粹主义概念的滥用与泛化越来越成为处于困境的西方制度自我辩护的手法,将失败归咎为民粹主义者的盲动似乎成为解释西方纠错机制暂时失灵的最好工具。
预言成真的政治游戏
世界进入民粹主义时代越来越成为对当下世界政治的流行解读。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时代的来临与民粹主义概念的滥用相辅相成。西方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危机的不断加深,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是这些危机的表征之一。由于本身的“灵活”特征及其概念的含糊性,民粹主义已经变成一个随意标签和贬低政治对手的标语,越来越多的涵义和内容被注入其中。这源自西方社会自我反思和革新精神的衰败,傲慢的西方建制派精英不愿意正视西方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将民众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满及国内外一系列反对派统一标签为民粹主义。因此,对民粹主义的滥用越来越成为压制社会多元声音的表现。这种态度既限制了自身可选择的危机应对措施,又激化了政治竞争对手间的矛盾,从而制约了各方沟通和协商的可能性,使得西方政治竞争呈现出从良性协商走向恶性斗争的趋势,社会进一步撕裂和极化。民粹主义浪潮越来越像是一种预言最终成真的政治游戏。
卡斯·穆德指出,“尽管对民粹主义的争论相当火热,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任何权威理论试图系统地解释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衰成败”。西方学界不愿去触碰民粹主义的“需求侧”问题,从心理上抗拒分析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而往往从“供给侧”角度夸大个人作用的主导型解释。随着疫情应对失败后社会危机的激化,对于民粹主义的滥用也出现了全面升级。